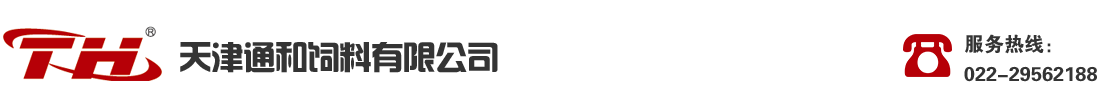许知远:年轻的生命力比学问重要
彼时,许知远37岁,还算年轻;书封上的梁启超更年轻,30岁。在众多同时代的书报中走近梁启超后,许知远看到流亡到旧金山的那位青年变革者,在以世界经验反观中国困境。三十而立的他逐渐脱离康有为,获得智识上的独立,也走到了思想成熟的关键时刻。从“维新”到“新民”,梁启超再一次推动了“变革”。
1903年9月25日,流亡中的梁启超抵达旧金山。“以军乐欢迎,盛况更过纽约。”第二天《旧金山呼声报》在头版报道了梁启超抵达时的场景,“梁启超乘坐早班火车从西雅图抵达……地方的代表团在十六街车站精心准备,欢迎他们的杰出领导人。”
这位“杰出领导人”时年30周岁,这是他流亡的第六年,他的一些和他同样年轻的朋友,六年前的变法失败后,被抓住砍了头。
110年后,也是一个秋天,旧金山迎来了当时知名度还不怎么高的许知远。按他自己的说法,当时的他“厌倦了新闻业的碎片与短暂,想寻求一种更辽阔与深沉的表达”,为此,他从北京搬到了旧金山。
在脱衣舞酒吧迷熏之余,许知远也常踱进哥伦布大街一家叫城市之光的书店。书店不大,却是美国著名的书店之一。许知远很喜欢去书店找欧洲文学的图书看。去得多了,他就和书架上的梁启超偶遇了——梁启超、泰戈尔和一位阿富汗思想家并列在某本书的封面上。
“梁启超正盯着我,他鼻正口阔,短发整洁而富有光泽,由中间清晰地分开,竖领白衫浆得笔挺,系一条窄领带,嘴角挂有一丝骄傲,眼神尤为坚定。”2019年,许知远在《青年变革者:梁启超(1873—1898)》的序言中回顾了他与梁启超的“偶遇”。
“梁启超正盯着我……”这样的叙述,能够理解为许知远自恋——9月23日下午,在长沙几何书店的新书分享会上,许知远坦陈了他的自恋。或是他的自恋,让他在对比了个人经验之后,觉得与梁启超“紧密相连”,并由此有了要为梁启超写书立传的想法:“为何不写一部他的传记,借此追溯近代史的转型呢?”
这便有了2019年出版的《青年变革者:梁启超(1873—1898)》和今年8月出版的《亡命:梁启超(1898—1903)》。从2015年9月开始写梁启超传记的第一行起,许知远便把梁启超与他的时代当成了自己生活中的一种平行存在。旅行到梁启超曾行经或驻留过的地方,许知远会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自问:“梁启超会看到什么景象?”
许知远甚至把梁启超的行动与思想,当作他的避难所:“读到他信中那些抱怨,看似成功的书报亏损不断,在同门面前忙于自辩,我感到某种释然,甚至对自己的创业焦虑不无缓解;他囫囵吞枣地应对立宪、文明、经济、笛卡尔、格莱斯顿、卢梭这些概念时,多少就像是我突然被抛入了大数据、OpenAI、埃隆·马斯克的世界吧。”
写梁启超传记、与梁启超平行的时段,恰巧也是许知远不断出品《十三邀》、不断与《十三邀》的嘉宾平行的时段。《十三邀》的粉丝应该感谢梁启超,若不是梁启超对许知远焦虑的缓解,《十三邀》能否连续出品还很难说。
《亡命:梁启超(1898—1903)》是许知远计划中的五卷本的梁启超传中的第二卷。这一卷的时间跨度是1898年秋至1903年夏,这是青年变革者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的第一阶段。六君子血洒菜市口,光绪被囚瀛台,一众同志四处逃散。他带着幸存者的内疚抵达东京。他要消化这创痛,也要警惕这创痛。流亡是前所未有的经验,熟悉的世界陡然消失,惊恐与威胁从未消退,对他头颅的悬赏遍布中国沿海城市,并延伸至海外。
相较于第一卷,《亡命:梁启超(1898—1903)》在结构和叙述上,技法更见纯熟。过去,大量的英语阅读,让许知远的中文表达也有较明显的“翻译体”风格。在写作梁启超传记时,他大量的外文阅读经验就帮了大忙——写作过程中,许知远特别开心的经历,就是用各种准确或不准确的梁启超拼音去数据库检索,发现之前没人注意到的一些对这位“杰出的中国流亡者”和“光绪皇帝的助手”的报道。这些报道或采用,或不采用,但都对许知远了解那个时代有裨益。
许知远坦陈,历史研究方面,他是门外汉,但他也无意去做一个专门的历史研究者去做的事情,如果说历史学家做的是对历史人物的思想和具体经历的考证,那么许知远更想做的,是对历史材料的重组,“我心中伟大的历史学家都是充满想象力的,而且具有高度文学性。发现新的材料最重要,很重要,但你要能够把材料置放于一个恰当的时空里,使不同的材料产生有机关联。这需要一种想象力和才华”。
曾经多年的新闻实操经历,锻炼出了许知远对自己想象力和才华的驾驭能力,也让许知远习惯了把目标人物放置到时代中去打量、观察,他充分地描述时代情绪,以大量细节还原历史场景,既尽可能地展现时代的辽阔,又尽可能地深入到具体的事件现场和人物内心,许知远称这样的写作是沉浸式写作。他的写作缓解了《十三邀》等工作给他带来的焦虑,《十三邀》的拍摄和制作也给了他写作上的启发,“单纯的写作好像更靠近写的人和内心发生连结,但镜头是要非常明确地表现出这个空间的,所以我写的时候空间感显而易见”。
这样的写作,带来的效果是,读者在阅读的时候,像是戴了VR眼镜,走进了梁启超的世界,并随着梁启超来到了他所在的时代,近距离打量、观察了康有为、严复、孙中山、李鸿章、大隈重信、西奥多·罗斯福,以及温哥华的叶恩、新加坡的邱菽园、悉尼的梅光达等散落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,他们的热情与挣扎,演绎出一部19、20世纪之交的全球风云画卷。画卷中,时运、国运、个人命运的升降沉浮,似就是那个时代的事,又似有很远的延伸。
许知远:最意外的是“保皇会”的那部分的。之前我没有想到它在海外有那么大的一个华人群体网络,形成了那么大的一个政治、商业组织。这是之前我们触及梁启超的时候很少触及到的。大家总是把他局限在一个思想人物去看待,而他作为行动者的这一面,展示得不多,他其实有着非常大的组织能力。
另外,他的全球旅行者的身份也是非常惊人的。我们大家常常以为他是在书斋里写东西或者编杂志,但他一直是高密度的旅行者。
许知远:1870年,世界开始了第一波全球化——之前其实也有,郑和下西洋、达伽马寻找香料、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等,是最早的全球化的一些行动。但是19世纪中叶之后,当时的轮船、铁路和电报带来的交通和通讯上的“革命”,形成了一些全球性的经济组织、全球性的市场。海外华人就生存在全球化的市场中,并在其中寻找到了自己的角色,海外华人系统又支撑了康梁的一些行动。所以,你看,梁启超的阅读、思考、行动,都是借助于全球化的这么个系统才能完成的。
潇湘晨报:梁启超的思想能够在当时那么快地传播出去,也是因那时已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传播网络。
许知远:对,他当年办《清议报》《新民丛报》,报纸很快就从横滨运到了上海,又从上海很快就分发到了全国各地,它的发行网络也是全球性的,在夏威夷也能买到,在温哥华、古巴也可以买到。
潇湘晨报:您在书里有提到,当时能够救中国的,是海外的那一拨人。您这么认为,是不是觉得当时海外华人已经有了全球视野,而同时代国内的人眼界受限,所以也不大可能能够真正意义上救中国?
许知远:对。像梁启超的老师黄遵宪,他作为驻外公使、外交官,去了美国、日本、新加坡,他对中国的看法和同时代官员很不一样,他展现出了一个新的视角。梁启超更是了。他被迫流亡,突然被抛到一个全新的思想世界里面,仅仅几年时间他就遥遥领先于大多数同代人——他获得了一个新的视角,对一个思想者来讲,新的视角是多么重要。
潇湘晨报:看您的这本书,让我很感慨的另外一点是,梁启超、谭嗣同等这拨年轻人,在那么年轻的时候有机会去做那么重要的事情。
许知远:因为甲午战争摧毁了过去的权力结构,整个官场体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裂缝。之前同治中兴形成的官场,甲午战争前当朝的很多官员都七八十岁,甲午海战失败证明当时那个官员系统不行了。裂缝形成后,一定是最敏锐的、声音最大的人物和力量能进入到舞台上。康梁他们本来是很边缘的人物,但他们也是因为在广东、在上海的原因,有新的视角、新的活动能力,所以一下子就被推到了那个位置上。其实,我们历史上经常这样子——身处改革转型的时代,旧的东西突然被淘汰掉,不发生作用了,让出一大片空间。比如,梁启超作为《时务报》主笔,他谈论的内容是新学问,是之前很多学问比他好很多的人没有接触过的学问,这时边缘者往往会更有力量。边缘人有着天然的优势,他们没负担。就像近些年,最先进入互联网、新媒体的那拨人,都不是最中心的媒体人。同样的,当时海外华人,在中国社会变化中也是很边缘的,他们不会想到有一天会发生及其重要的作用。孙中山说华侨乃革命之母。华侨怎么会对中国革命产生影响?一般的情况下不会的,但是帝国中心的衰落带来了契机。
潇湘晨报:在写作梁启超的过程中,他的性格、行事风格等有没影响到您?你有没有从他那里获得过力量?
许知远:梁启超比我想的有韧性。他经历过很多失败,不断地失败。这些失败在他的人生过程中都变成了新的养料,理解中国和世界的养料,也是支持他下一步行动的养料。他从来就没被失败摧毁,他有一种反脆弱的本领,能把困境、缺陷和对他的攻击转化成一种新的力量。这样的人很少见,孙文也是这样的。
许知远:各种都行——我挺想让他们觉得人生会有多种可能性,即使在一个巨大的灾难或者困境中,仍有很多种可能性,仍有人的自由意志。
我觉得这本书挺励志的,梁启超是一个失败的连续创业者,他参与维新运动、戊戌变法、流亡,也就是23岁到30岁,虽然那个时代的人比较早熟,但也是很年轻的一个人。我觉得年轻的生命力比学问本身重要多了。